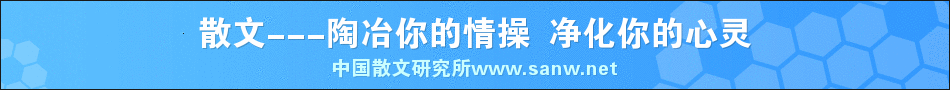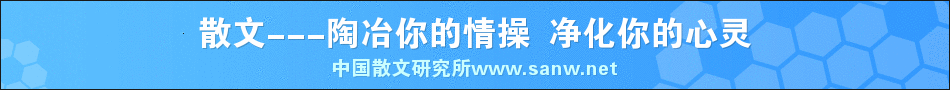黑颜色
文/素素
那座山岭一直在远处诱惑着我。
那座山岭原本不叫那个名字,因为有人写了一本书,它便与一个土匪和一个英雄的名字连在一起,成为一座真实的山岭。
其实随着匪首就擒和英雄凯旋,那座山岭便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大雪的早晨坍塌了。然而,那座山岭又永远地耸立着,成为一个见证,一个注脚。山东出响马,关东出胡子。响马和胡子都是土匪。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土匪确曾充斥了东北,人们在想象东北的时候,总会在那一望无际之中,看见一支支凶悍残忍的马队,看见一张张野性的布满杀机的脸。这或许就是我一定要去寻访那座山岭的理由吧。
我是从佳木斯去牡丹江的。小火车走得很慢,几分钟就停一次。车上没有女乘务员,只看见一个不到退休年纪就已经很老的老人穿着铁路标志的服装在过道上偶尔地走过去。那节卧铺车厢只卖了中下铺,我要的是中铺。我的下铺是一个壮实而且有点精明之气的老人,对铺两个是衣着还算体面的青年人。大家都不说话。这将是一天的车程,一天里为了不上厕所,我一口水也不喝,午饭是两颗香蕉。下铺的老人将这一天过得十分从容,刚坐下就在茶几上摆出一个装着小咸菜和花生米的饭盒,接着又摆出一瓶榆树大曲,一包力士牌香烟。我躺在中铺悄无声息地看书。一会儿,烟味上来了,那老人在抽烟。一会儿,酒味上来了,那老人在喝酒。一会儿,呼噜声上来了,那老人睡了。过一会儿,烟味又上来了,酒味又上来了,呼噜声又上来了。一天之中,它们周而复始。我根本没去注意那两个年轻人,他们太文弱,目光里似乎也有一丝怯意。老人身上却有一种原始的让人害怕的东西,他太像那本书里写的那个人物。但这一天什么也没发生。快到牡丹江时,我从中铺安全地下来,又安全地坐到过道的折叠椅上。当我面对面看着烟味酒味的老人时,我发现他的眉目之间大量散发着慈祥的内容。分别时我将佳木斯朋友送的一袋子水果转送给他,他说声谢谢,没有推辞。
我之所以要如此细致地描绘那节卧铺车厢的情景,是因为我从走进东北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我以为,任何一个女子,当你独自一人在大东北的平原或山林里行走的时候,都会感到那种无所不在的恐惧。你总是被那个悠长的黑色的阴影笼罩着,并产生联想。
要知道,我前方要去的是威虎山呵!
那天,我约了牡丹江的两位朋友一起去做这次旅行。与我一样,威虎山在他们心中仍是传奇。对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旅长座山雕,仍是在那本书、那个电影、那个样板戏里获得的印象,对我千里迢迢的寻访既感到惊讶又表示赞赏。威虎山就在距牡丹江几十公里之近的海林,他们无数次去过海林却从未去过威虎山,所以他们撸胳膊挽袖子仿佛进山剿匪一般激动。
记得我是在小学5年级时从同桌的男生手里借到《林海雪原》。书主明令我必须在第二天早上打铃上课前把书还他,否则不借。那个晚上,我直等到母亲上炕睡下,才谎称复习功课把饭桌安放在母亲烧火做饭的灶坑前,添满了灯油,开始看那本盼望已久的大书。我一夜未睡,终于赶在母亲起来做早饭之前将书看完。照照镜子,脸让灯的油烟呛成黑色,两个鼻孔更黑。就在那个晚上,我与英雄和土匪相识。对英雄是爱,对土匪却也不只是恨。我更多是想,那片林海雪原里怎么会包藏了那样一种人生!
如今写土匪的书早已不止《林海雪原》,写土匪几乎成了时髦,成了东北人的一种炫耀。那团已经飘逝了的黑颜色,又重新被搅起。东北原本就没有士大夫文化,俗文化一直就是汪洋大海。城里的出租车司机,乡村的马车夫,每天最爱听的就是写张大帅吴大舌头的小说连播《乱世枭雄》。东北的土匪被以通俗的方式描写着,并以通俗的方式传播着。土匪成为东北俗文化里最叫座的文本。我再也不是初读《林海雪原》时的心情,打开东北,它有许多经历,许多故事,土匪绝对是它永远的尴尬和缺憾。
中午到达海林。海林因为县改市,又新建了不少高楼大厦,满街都是“威虎山”招牌。威虎山小吃店,威虎山大酒楼,威虎山牌啤酒,一个比一个逼人,让我觉得我已经进山了,已经离那个松柏参天、奇峰异洞、九群七十二地堡的匪窝很近了。这很可理解,那座山岭让这个毫无个性的小城市有了个性,让没有机会的今人有了机会,他们终于可以放纵地演绎现代欲望。曾经是灾难,现在变成吉祥。
带我们进山的海林朋友是位局长,他手中很奇怪地拎了一瓶红油漆和一只小刷子,我们坐上一辆北京吉普出发了。威虎山在《林海雪原》之前叫大夹皮沟,小说家在写这个故事时将吉林的威虎岭挪到了这儿,从此大夹皮沟就叫成了威虎山。然而吉普车跑了将近一个小时后,在距威虎山不远的地方,仍看见了一个名叫夹皮沟的小镇,临街的几间小店铺,门旁挂的牌子都冠以夹皮沟字样,好像怀旧似的,告诉你夹皮沟还在。吉普车没有停留,我的目光却久久地徘徊在那条寂静的街上。我想,李勇奇一家说不定还住在这里。
车继续向山的深处驶去。直到在一条幽长的被蒿草遮闭的毛毛道上实在开不动了,我们才下车徒步,大家拨着人一样高的蒿草又向前走了望二十分钟左右。终于,眼前出现了一块刻着“威虎山”三个大字的石碑。字是用黑色的漆涂的,快剥落干净了,可见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来过,可见人们对威虎山的态度曾经是保守的。这时,局长朋友拿出了他带来的红油漆和小刷子,原来他此行的另一个使命就是把威虎山由黑字涂成红字。
然而,这就是威虎山?
它只是很远,却并不高峻。一条长长的山沟,两侧如壁的山岭,使它更像一个宅院。我们访客一般走到它的阶前,平常得让人倦怠。绕过那块石碑,局长朋友带我们向半山腰爬去。山腰的平坦处,有一个支离破碎的窝棚,附近还有一眼寂静的山泉。局长朋友说,这就是当年座山雕的威虎厅,不过是一个地窨子,座山雕被杨子荣抓了后,他的老窝就塌了。后来,因为出了那本书,林场工人怕人们忘了那地方,就在土坑上支了个窝棚。那块石碑也是后来才有的。
曾经是一个既令人惧怕又让人向往的诡秘之地,居然是如此的朴素无奇。原先的那种兴奋顿然消失,几个人在那座山岭上呆坐了很久。四周静极了,动的只有蝴蝶。草尖上,野花瓣上,无数的白蝶黑蝶花蝶飞来飞去。蝴蝶让我想到了女人。我明白了那个女人为什么叫蝴蝶迷,为什么这一带许多女匪首都叫蝴蝶迷,在清一色的山里,在清一色的男人堆里,蝴蝶的确是女性的。
那蝴蝶还让我想起另一座山岭上另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二十年代吉林的一个著名女匪,被官兵捕获后在长春三马路东头荒地执行枪决。那个场面曾经震惊全国,上海《申报》写道:当其押赴刑场时,该匪身披大红库缎平金猞猁斗篷,内穿宝蓝狐腿旗袍,头戴白皮暖帽,面不改色,貌颇不恶,殊不知其杀人不变色之悍匪也。观刑者人山人海,该匪站立囚车上,向众人曰,我名张素贞,驼龙系我外号,今年二十五岁,奉天辽阳人,十九岁下窑子,大龙花三千元替我赎身,遂跟大龙前后为匪六年,死我手下者不知几千人,一个娘儿们,能纵横数百里,屡抗官兵,总算露脸了,今又承诸位盛情走送,谢谢......一个女匪,在这里被描写得凤鸦难辨,而且她一直就成为一个谜。东北的男人女人,几乎没人不知道这个大号驼龙的女人,她的人生在各种版本的书里翻印着,她成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通俗小说家猎奇的对象。我只是不明白,那么美丽柔软的女人,灵魂为什么突然就能撕裂,手为什么突然就能杀人如麻。人是多么神秘呵。在人性深处,善不可测,恶更不可测。然而,让女人以这种方式沉沦,能说不是东北的悲哀吗?
称霸山岭的当然是男人,但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眼前这座山岭曾经是一个有着四十年胡匪生涯的座山雕的巢穴,面对着它,我看见了一个老土匪的纯粹和顽强。在此之前,我去过沈阳张作霖的大帅府,读过一本描写吉林夹皮沟著名金匪韩边外家族的书,张氏韩氏都是由土匪起家,又由土匪而进入政治。他们双手沾着血从山岭上堂而皇之地走进城市,走进官场,走进大庭广众,走进东北的野史。他们是另一种土匪。座山雕却是一个真正的土匪,他永远守在山岭,山岭是他的信仰。听说,当他被杨子荣从那个阴暗的地窨子里活捉时,目光里有一种梦醒般的沮丧和不甘。在监狱里,他不吃不喝,也没有语言,一直到死,圆满地完成了一个老匪巨匪的悲剧。
在东北部那片山岭里,蝴蝶迷有许多个,座山雕也有许多个。座山雕是一个符号,一个代名词。在近代史上,他们盘踞了东北,让东北有了一个独特的盛产土匪的时代,土匪居然成了许多男人的人生理想和英雄情结。最多的时候,曾有几十万男人加入此列,大匪小匪,密集如蚁,东北承受了一次恶性的繁殖。养儿当土匪,是东北作家萧军的小说里写过的一种奇异的乡俗。南方出身的林语堂在《中国人》里则下过这样的定义:南方人是商人,北方人是强盗。精明与野蛮,一江之隔。在寒冷空茫的背景里,北方的男人已经被规定成一种角色。
在我的印象中,土匪这个字眼本身就隐含着不屑和蔑视。土匪,一曰土,二曰匪。土是乡土,东北的土匪与关内的土匪是两种装扮,关内的土匪外表显出一些儒雅,绸裤,皮鞋,墨镜,且油头粉面。东北的土匪则是叠裆大棉裤,狗皮帽子,乌拉鞋,土得掉渣。不论他们曾经是纯朴的,有良知的,侠义的,还是原本就属于流氓赌棍不逞之徒,他们是破落的东北牌农民。没有文化,只有信条。那信条是物质化的,或图官或图财或图享乐,他们为此而去巧取豪夺,将人性的丑张扬到了极致。
匪则是精神的丧失。任何宗教点化不了他们,有奶便是娘,效忠与背叛,在他们是游戏,是眨眼之间的事。在匪的世界里,此岸是黑色,彼岸还是黑色,黑色来自内心,来自灵魂,并指引着灵魂的方向。他们是精神的屠夫,又是肉体的杀戮者,曾经将东北蹂躏得体无完肤。那群人即使在后来消泯成白骨,他们的精神也总是要有一些遗留的。后代的东北人在大发豪气的时候,总让人疑疑惑惑隐隐约约地看出些匪气。
一个土匪时代,绝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东北的宿命。东北太特殊了,既是日俄两强觊觎的肥肉,又是关内移民者谋生的沃土,这片原本属于游牧者和猎人的领地一下子变成了被外忧与内患挤逼的夹缝。移民者本是最有生命气息的人群,但移民者内心裹藏的那种绝望,又使他们最具破坏力。在他们还没有扔下手中的讨饭棍,生存状态还相当严峻时,做土匪便成了一种极端的人生选择。我发现,那些可以叫出名字的老牌土匪,没有一个不是闯关东的移民者或他们的后代。当我把他们置入移民文化的背景里,我的心便被触疼了。这其实是移民者共有的心态,我知道许多人如我一样,在回望那段历史那一群人的时候,有可能惶悚,却不会觉得陌生。东北从来就不是梦幻的,我们祖先也不是朝圣者,他们成群结队地来,所面对的,就是死或者活。生的本能驱使着他们,东北于是被追逐和洗劫,喧哗和陷落。
那座山岭,此刻正浴满阳光。在我心中,却是一个沉重的景物。它永远不会被遗忘,也不会消失。就像历史。
晚上,我们坐在海林市内的一个小酒馆里,喝牡丹江牌白酒,威虎山牌啤酒。酒桌上就我一个女的,却不容分说,喝酒。先喝白的,后喝啤的。喝白酒时全桌共用一只啤酒杯子,轮流着给每人倒满一杯,一杯要一口喝下去。也许是因为刚刚从威虎山上下来,也许是因为这酒也是威虎山的,也许还是那些男人个个都太能喝,那个晚上,我身上潜在的野性被唤发了。那个晚上,我不知究竟喝了多少酒,只记得那杯酒只要轮到我这里,我就一饮而尽。那时的我,其实是在非常清醒地试探自己,我看见我这个外表文静的女人,诡怪而又陌生。
喝酒的人中,有一位曾在县剧团唱过少剑波,于是就有人唱杨子荣李勇奇。我则唱小常宝和李勇奇他妈。所有的人都大红着脸,所有的人都大嚎着嗓门,仿佛不这样就不是威虎山的人。朔风吹林涛吼。穿林海跨雪原。早也盼晚也盼。八年前风雪夜。先是如喝酒那样一个人一个人地轮着唱,酒喝多了就开始抢着唱,最后便是东倒西歪地唱。从来也没唱过这么多歌,从来也没醉着唱歌,大喝大唱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座酷风野习的山岭。
那次酒醒之后,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人类自己。那个喝酒的夜晚,不久也将变成一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