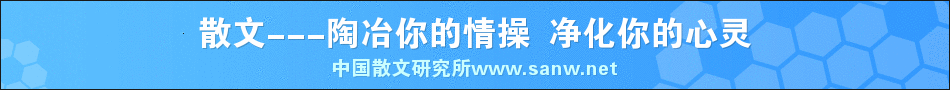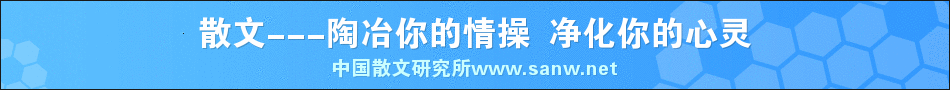火炕1 (2009-04-22 22:24:55)

转载▼
文/素素
在城市里已经住了二十年,一直是睡床。最初是睡女生宿舍那张双层的铁床,我在下铺,靠着北窗。窗外是渤海湾的一片浅滩浴场,冬天时岸边便堆满了雪白的冰。冰是波浪形的,带着大北风的痕迹。不远处就是不冻的灰蓝的冷调的海,咆哮着要登岸似的闹人。那张铁床就像搁浅在结冰的海滩上,人仿佛随时随地就能被风刮进海里,是一种彻骨的凉。宿舍每个女生都有一只热水袋,去教室上晚自习之前,必是先将装满水的热水袋放在被窝里,这样上床睡觉的时候手脚就能伸开了。毕业后便是在这个城市安家,铁床换成了席梦思。然而总归是床,最冷的日子,即使回到了家里,满屋子转来转去,也找不到最温暖的那一隅。
这时候,我就会想念乡村的火炕。虽然北山墙上挂着厚厚的霜,风吹得门窗直响,坐在火炕上,就不觉得冷。因为有火炕,乡村的男人女人都会盘腿。家里来客或是上谁家串门,进屋就上炕盘腿坐着。男人抽烟,女人做针线,一坐就坐大半天。乡村的孩子是坐不住炕的,他们要去河里滑冰车,到街上打雪仗,去茅厕时才发现手冻得连裤带都系不上了,便提着裤子跑回家,把手伸给正坐在炕上做针线的母亲。做母亲的则欠欠身子,将那两只红馒头似的小手坐在屁股下面,不一会儿就给焐热了。
乡村的火炕在北方的冬天里就是投靠和归宿。火炕让你有家,让你出去了还要回。床则像房间里的一个布景,不能随意触摸,也不能依赖。床让你永远是客,不论什么时候,打起行装就可以走。
对于我,想念火炕就是想念童年,想念纯朴的母爱,想念只有在火炕上才能发生的风景。在乡村里出生的孩子,离开母体之后第一个承接他的不是医院里雪白的产床,而是火炕。老式的火炕上面铺着苇席,苇席下面再铺一层谷草,谷草蓄热而且暄软。乡村的男人和女人,一生都在这样的火炕上纠缠。他们在灼热的火炕上毫无节制地纵欲,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让孩子诞生。火炕太能容纳了,每一铺火炕都人口密集。那年我七八岁,我问二嫂的肚子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大,二嫂说那里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小人儿。果然那天早上再去敲门时门就不开了,我趴着窗子向屋里看,二嫂家的炕席被卷起来了,她赤身躺在谷草上,在那焦黄的谷草里,蠕动着一个鲜红的动物般的小身体。二嫂的婆婆也就是我的伯母端来一盆水,她一眼发现我在偷看,立刻爬上炕拉严了窗帘......我想,这大概也是我出生时的情景。火炕上谷草焦黄焦黄,我便如母亲说的那样,落草为人。
直到现在,乡村的男人女人虽不再为生育而繁忙,却仍贪恋着火炕上的情欲,仍在火炕上无尽地纠缠。火炕是他们的圣地,是生命的摇篮。
火炕是母性的,它更多的时候属于女人。在东北的乡村,分炕上活儿和地下活儿。东北寒冷,东北男人多女人少,东北的男人宠惯女人,而早年的女人又是小脚,地下活儿大多由男人干,拉犁种地收庄稼挑大粪跑买卖,男人大包大揽。女人做炕上活儿,缝衣絮被绣枕头纳鞋底儿,女人们都是在炕上完成的。女人比男人更能坐炕,女人坐炕坐得滋润,她们那两条腿即使穿再厚的棉裤也能柔软地盘上。
未出嫁的姑娘冬天里爱聚堆儿,她们互相抄花样子,绣枕头绣门帘绣各种各样的罩子。我姐姐出嫁时绣了两种枕头,一种是洋枕,细白布,带飞边儿的,一种是方枕,家织布,从在旗人家里学来的。我家那地方把满族人叫成在旗人。在旗人的方枕六个面八个角,两头的沙式刺绣很好看,就是枕芯太硬,出嫁的姑娘并不枕它,但柜子上一定要有它做摆设。她们没白没黑地绣,把炕坐出坑了。已经做了嫂子的女人把饭端上桌子,她们才把绣架一放,坐过来吃现成的,那做哥哥的就拿眼角白她们。她们出嫁那天,拜完天地就坐炕,婆家人在褥子下面放一把斧子,再硌人也得把“福”坐住。
做了媳妇的女人,冬天里最忙的活儿是做鞋。给公公婆婆小叔小姑做,给男人和孩子做,最后才是给自己做。穿了一冬的棉鞋棉乌拉,在大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时一定要换上一双家做的新布鞋。家口大的,一个女人要做十几双鞋。这个活儿其实从夏天就开始了,选在大热天的中午,打好一盆面浆糊,拿出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布,摘一扇堂屋的门板,然后就一层浆糊一层布地裱袼褙。当那一块一块的袼褙在夏天的大太阳底下晒透了,便卷起来留到冬天做鞋底子。纳鞋底儿的麻绳也是在夏天就备好了麻匹,冬天要做鞋了,提前几天几夜地赶着搓麻绳。搓好了就拧成麻花劲儿串起来挂在墙上,纳鞋底时一根一根扯下来用。纳鞋底儿是力气活,未出嫁的姑娘怕把手勒出泡,瞪眼看着嫂子挨累也不伸手去帮。那做嫂子的坐在炕上简直就是牛马一般,任那麻绳勒破手。她们已经嫁了,粗糙就粗糙吧,好在男人并不嫌乎。男人做崐地下活儿就一阵儿,女人的炕上活儿没有头。男人晚上回家吃完饭就上炕睡觉,女人还在灯下纳那纳不完的鞋底。知道疼的男人会说一句:炕上活儿比地下活儿累多了。灯下的女人听了,鞋底儿纳得就更欢了。
睡火炕可以看见男人的权威。火炕分炕头炕梢,炕头靠锅台近,炕一宿到亮是热的。炕梢离锅台远,不到半夜炕就凉了。乡村人睡炕不铺褥子,身子就贴在炕席上。大人认为小孩火气旺,不怕睡凉炕,所以占据炕头的总是这个家的男主人。挨着的是女人,女人的旁边才是孩子。如果孩子多,就从最小的开始往下排,炕梢当然是最大的孩子或者是女孩子。女孩子未成年时还能与父母兄妹在一铺炕上挤,成人儿了便要独自去里屋睡。里屋炕更凉,凉也要去,女孩子天生喜欢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炕头永远是男人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东北乡村男人的幸福观。白天与牛在地里忙碌,晚上与女人在炕上忙碌,那男人终于累了,他就理所当然地睡在那炕头。用热炕头去烙他那疲惫的腰身,酸痛的筋骨,困倦的精神。经过这一夜的烘烤,第二天起来又是一条硬汉。每天每天,日子就这么重复地过着,直到他在那个热炕头上再也爬不起来,成为行将就木的老人。
烧火炕用的是柴草。我小时候,最累的活儿就是拾草。我的老家不在平原,也不在山岭,而在光秃的丘陵之间,小孩子放了寒假惟一的活儿就是拾草。所有的孩子都拾草,那些光秃的丘陵就更加地光秃。近处的草拾净了,就向远处出发,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已经走到几十里地以外的山场子了。山场子的柞树也并不茂盛,地上的叶子很快就光了,我们就用手去摘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也摘光了,我们就刨树下的草根。草根刨光之后,土就露出来了。山场子一片破败,而我们拾草的队伍还是浩浩荡荡。那么小的孩子,要管全家的烧草,叫“供锅底儿”。
我曾经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祈祷》。我的祈祷非常单纯,不是福也不是财,就是请上帝赐给我一个有力气的大兄长,让他帮我拾草,或者让他在我拾草回来的路上迎一下,替我背一会儿沉重的草包。那时,我的背上总是有一个大锅般的草包,鬼一样地在山路上慢慢移动,累了也不敢放下,而只能在有短墙或斜坡的时候倚靠一会儿,因为没有人来迎。那时我太羡慕那些有哥哥的人,有一个庄稼院的老父亲也好。记得每次回到家里,饿得那么厉害,扔下草包并不是想吃饭,而是先大哭一场。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累和孤独,直到现在我一边写它一边还在流泪。
我之所以哭过之后还是要去拾草,都是为了母亲。父亲在城里工作,过度辛劳的母亲得了腰疼病,我必须拾很多的草,让母亲做熟一家人的饭,让母亲能睡上热炕。如今我早已不再拾草,然而我不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一丛茂密的蒿草,一块深秋的苇塘,只要那是可以当柴烧的,我就想去拔去割去搂,那态势就像卓别林到处追赶着拧螺丝。我的某一根神经至今仍停留在童年的贫乏和痛苦之中。
关于火炕的记忆太多了,它已经温暖了我们两千多年。更重要的,火炕是东北土著沃沮人的发明。我是在翻阅团结文化的有关章节时发现这个秘密的,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曾经手舞足蹈地兴奋了好久。我觉得火炕就应该由东北人发明,东北人就应该给人类创造出这样一铺火炕,这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自然而然责无旁贷的事。试想,在人少兽多的时代,为躲避凶猛野兽,祖先们只有在树上巢居,美其名曰有巢氏。当他们学会制作石刀石斧之后,才从树上跳下来住进洞穴。大东北有很多古人类洞穴,金牛山洞,鸽子洞,还有古代大鲜卑山上的嘎仙洞,都曾是东北人祖先住过的家。但那时他们只能围着篝火睡觉,还不曾有真正的安眠。直到从山顶走向平原,在平原上挖出地穴或半地穴式的居所,才睡上了火炕。或者说,有了火炕,才有了地穴居或半地穴居。
这是东北古人类的一个新纪元,是严寒和冰雪赐予了他们灵性,他们又以火炕的方式拯救了自己。因为当火炕在地穴深处散发出热量,他们才试着从地穴里升出地面,让古老的荒原上出现了亮亮堂堂的房屋。房屋绝对是火炕催生的风景,它使人类的居住史发生了巨变,使人类从此有了尊严,从此见到了阳光,终于由胆怯的动物般的生存,过上了人的体面的生活。
火炕是真正的东北土著文化。虽然我只能从所剩无几的历史遗迹里去猜想两千年前的火炕造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火炕一旦被知道,被效仿,它就变成了华夏文明的瑰宝。事实上,正因为有了从大东北传来的火炕,才使华北、大西北以及整个北方各民族的人们一同从地下爬出地面,这世上才有了各式各样的火炕。只是,那时不会有人知道这是沃沮人的发明,也就不会有人向发明者道声谢谢,文明是共享的,沃沮人当初不是也曾享用过中原人发明的犁铧吗?
反正那些日子,不由自主地,我总是暗自为火炕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