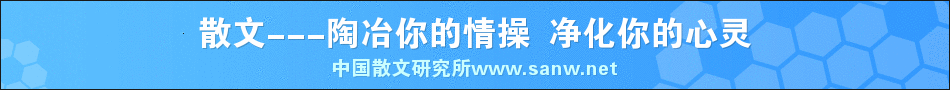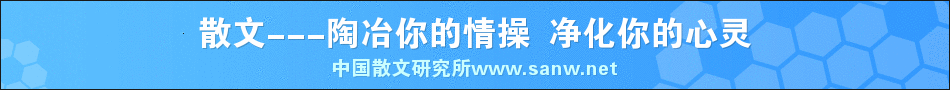线团是个起跑的姿势
一、线团是个起跑的姿势
从前,现在仍然是这样:我喜欢拆旧毛衣。说我喜欢拆旧毛衣也不准确,我有时拆的是新毛衣。看来我拆毛衣的理由并不是毛衣旧了。
很少有特别完美的毛衣。每一件上面,都可以找到一些毛病:式样过时、缩水了、变形了、太瘦、太肥、太旧了、花纹看腻了……——这些都可以成为我拆掉它们的理由。有时候我想织一条围巾,我就会在那些毛衣里找,看哪一件的线更适合织围巾。
我为什么不去买一些新毛线呢?当我要织一个什么的时候,为什么不去买一些新毛线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谁知道自己的一些特殊嗜好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的很多用其他布料制作的衣服,我也是很想把它们拆掉的。只是棉布、毛料、丝绸等衣料,拆开后不能还原成一块完整的布料。它们回不去了,这就是我不拆它们的原因。
毛衣不同。——毛衣是一种特殊的衣服。拆掉后能还原成原来的毛线。一团一团,像新的一样。像从来不曾被织成过毛衣。
我拆一件毛衣时,内心很快乐,甚至充满了激情。我不觉得那是一件麻烦的劳动,而是在纠正一个错误。而这个隐藏在我生活中的错误,被我这么修改了后,我的生活会更完美、没有瑕疵。
我拆毛衣的行为,很有象征意味。我对一些大的事情也是不满意的,但我无力修改。而拆掉一件我认为有问题的毛衣是多么容易。我通过拆毛衣证明我有能力修改错误,从而掩盖了我对有些错误的无能为力。
毛线刚拆下来时,那些线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勾弯。那是它们过去的形态,都是一些坏习惯。我无法忍受毛线变成了那样。我用开水来烫那些错误,也就是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这是个残酷的办法,但是你劝说那些勾弯,它们是不肯自己伸直的。毛线的一些经历包括我认为的错误、细菌、病毒,都在热水里死了。毛线干净了,伸直了。它们在热水里转世、脱胎换骨回到了过去。回到起点。回到没有错误的童年。
然后是晾晒。它们一束束在阳台的光线里滴着水。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过去的污迹滴下去,把过去的一切滴下去。
几个小时后,平展、蓬松的毛线在太阳下晒干了。
我把它们套在脚上,以手为中心把它们缠成线团。它们被团了起来,做好了一个起跑的姿势。——线团是个起跑的姿势。
这些年来,我沉迷于拆毛衣。我用手指的轻柔动作,就把过时的花纹、编织的错误、缩水变形等一系列问题删除了。
在我的衣橱里,你是找不到几件毛衣的,但你不用找就会看到很多溢着香味的线团。它们这里一团,那里一团,像是一些顽童,随时会蹦跳、滚动,开始新的生活!
二、里面的扶手
说有一个女人,怀孕了。她小心翼翼地怀孕,什么活都不敢干了。她每天吃饭动动嘴,洗脸动动手,其他的部位都不敢动了,怕惊动肉体深处那个刚刚坐了窝住下来的小鸟。好几个月过去了,那只小鸟感到很安全,房子很稳固,外面刮多大风,屋子都不摇晃。小鸟很满意,不打算飞走了。小鸟的想法女人知道了,她通过辨认肚皮上的花纹看出了小鸟的心思。怀孕的女人放心了,同时也大意了。一天,她睡了一个很好的午觉。醒来后,见阳光在窗外明媚,幸福感集中在女人胸腔内的某一腔室,它们想与室内光粒子结合,形成雾霭后,对女人进行长久的笼罩。女人伸了个懒腰,那个幸福气团随肌肉的运动弥漫全身,然后从每个毛孔溢出,然后一颗一颗地与光粒子结合。女人把两条胳膊慢慢向头顶伸过去,同时舒展开一直紧张弓着的腰部,腿尽可能地往下伸直,向后弯曲,像虾遇热后的尾部。女人就这样伸了一个蛇蜕皮般由多组微小动作组合的懒腰,结果,她流产了。
这个故事是我听到的,给我讲述的人我认识,被叙述的人我也认识,所以这不是我虚构的。我无法想像伸一个懒腰,会是一个流产事件的起因。这和我的直接经验出入太大。我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还在骑自行车,并且和车一块摔倒过。我从地上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把翻到在身边、后轮风转的自行车扶起来,正了一下向左歪了的车把,骑上继续走。上班快迟到了。那时我是团区委的组宣部长,赶着去开一个会。此后类似事件又发生过。我经常给肚子里的我儿子来一场7.6级左右的地震。我不是故意的,因此没法事先通知他准备好。每次我都担心他会掉下来。
他一直没有掉下来。他在里面安装了扶手。他每天牢牢抓着那扶手,任我怎么摇晃、震荡,他都牢牢地悬挂在那里。应该不是我怕流产,而是肚子里的孩子,他怕流产。他找到我这样一个妈,一定非常满意,天天在里面偷偷乐。他担心我会甩掉他,就居安思危,在里面四处寻找扶手。扶手找到后,抓住就再不敢撒手。后来他像一只猴子,稳稳地坐在树杈上,双手抓住树枝,大风吹来,他同大树一块摇晃。十个月后,他长成这棵树上唯一硕大结实的果子,平安地滑落到松软的泥土地上,一面红,一面绿。
那些打个喷嚏、伸个懒腰就流产的孩子,那是因为那孩子后悔了,对你这个妈不满意,他在里面故意什么扶手都不抓,他想找个借口离开,但总也找不着,最后没办法,你伸个懒腰就成为他抛弃你的理由。人家是寻找理想的妈去了。
流产的孩子,都是发觉错误立刻就改的好孩子。
三、分身术
12年前,我在吉林市船营区城建局绿化科上班。我是内勤,负责绿化科的内部事务,而外面的事由科长来做。科长是男的。我们绿化科就我和科长两个人。这有点像一个家庭:女主内,男主外。科长喜欢养鱼。办公室靠西墙有个大鱼缸,里面养了六条地图鱼。他还养花,地中央一盆龟背竹,长得四仰八叉。每片叶子都有点像一只绿乌龟。叶茎很长,这样就使每片叶子都在花盆的四周一两米的地方悬着,真有点像一只只乌龟以花盆为起点向四周缓慢爬行,它们被身后的那条绳子拽着,这样,它们都爬了好几年了,才离开花盆一两米远。
我每天看鱼,检查输氧泵是否正常工作,检查水的温度。地图鱼是热带鱼,对水温有要求;给龟背竹浇水,把爬得太远的叶子拢回来;还要擦桌子、擦窗台。科长的桌子我也给擦,但是如果哪天他惹我生气,我就不给他擦桌子。更主要的工作是接电话,有事的时候往出打一打电话;有居民上访的,做记录并处理一下。上访的不多,并不是很多居民都和他们家附近的树木发生纠纷,大部分人还是能和树木和平相处的。总之我没多少活干。而我感到工作没什么可干的时候,正是想干点什么的年龄,那时我三十多岁。
虽然这些工作不需要有大脑,也不需要什么体力,但是你得天天去,你的身体得坐在那把椅子上。我的大脑也得天天跟着去,虽然大脑不需要启动。我也没办法把大脑单独留在家里,告诉她这样的工作不用劳她大驾。而我的大脑正处于爱运动的时候,不让她启动它很心烦,后来也不管需不需要,没征求我的同意就自作主张启动并运转了起来。
我的大脑私自启动并运转的结果是,它给自己又起了个名字,并用这个名字写出很多文章。她还让我的身体行动起来,把这些文章寄给文学杂志社。而杂志社的人都说这文章写得好啊。这样它们都发表出来,并且被很多人读到了。
后来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局面,那个叫格致的写文章的人,几乎成了名人。很多人爱读格致写的文章。这件事一直是个秘密。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的家里人不知道,单位的人更不知道。尤其不能让科长知道。你天天坐那呆着行,你要做了别的事,那你就是不安心工作,尤其我的工作做得也不是一点不足都没有。
可是我也想老老实实地擦擦桌子,看看报纸,给龟背竹浇水……,可我管不住我的大脑,它太爱动了,像个不懂事的小孩一样。
我天天擦完桌子扫完地,看看科长又出去了,并且三个小时之内不会来,我就开始写文章了。我的文章源源不断地被我写出来,供给那些我不知身在何处的人阅读。我感到这很有意思啊!偷偷摸摸干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
我们单位也有三十多人吧,他们谁也不了解我。我也不敢让谁了解。我成了个有秘密的人了。
我在办公室写文章最怕让人看到。我最怕谁没事跑我这来聊天。也总有人来。我怕人家说个没完,就不敢多和人家说话。我总是说一句答一句。人家就觉得和我聊天聊不恋呼,也就不聊了。
我每天靠写文章供养格致活着。她是我的替身,用文字喂养。我越来越觉得格致存在有意义了。我整天为她着想,为她提心吊胆。我觉得和一切都值得。如果我每天只擦桌子、扫地、打电话,而没有这个秘密的、鬼鬼祟祟的事情做,我就感到活着没有多少意思了。
这个格致是被我生生叙述出来的。格致是违法的,当然是违法的,格致到现在也没有身份证。格致在法律上不存在,但在读者中存在。这是一种颤巍巍的存在,是一种随时可能消失的存在。我有多紧张!认可格致存在的人越多,格致就越安全、越牢固。
我此生是依赖替身活下来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不明原因无法医治的疾病,被大神宣布活不过18岁。我是大神说的花姐。要以处女之身夭折。这是天规定的,但是我妈不愿意。他和大神一起反对天意,偷偷制作了一个我的替身。多年以前我的替身就已经替我上了西天,每天为王母娘娘递茶打扇。做一个天神的侍女。这么多年了,她没有被察觉。于是我活了下来,活过了十八岁,竟然活到现在这么老了。
那个天上的侍女是我的替身,这个格致也是我的替身,加起来我有两个替身了。她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肉身,没有肉身她们自由,上天入地、深入人心。
看看我活得有多复杂。需要这么多替身帮我活着。我活着是我和我的替身们共同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显然我已经把自己整成了一个复数:天上一个;地上一个;汉字里一个。
——而地上的这个会最先死掉。
如果地上的这个我死了,天上的那个、汉字里的那个还不死,那就等于我没死,或没能完全彻底地死去。——那么我的死亡过程就会被拉长。地上的我把死亡拉开序幕之后,其他的我如果不能跟上我死亡的脚步,那么我的死就不能结束。我的死亡过程也许会比一些人使用的时间多。一个简单的死亡,在我这里甚至会成为一件不那么容易结束的事情。——我为我能在我的死亡过程中更多地使用时间而感到有趣。
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一个成人游戏。
还有一种不好玩的可能,那就是,我还没死呢,汉字里的格致先死了。如果这种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这个游戏就没法玩了。我不愿意看到我的替身先我而死,我还要为她送葬,为她悲伤。会怀疑我存在的价值。这会导致我的死亡速度太快,快到追上了肉体的死亡。
这就不好玩了,这就与大部分人一样了。我得想办法让我死得慢一些、要让我的死亡减去肉体的死亡还有所剩余。
那么我得好好写,我知道我写得越好,她就活得越长。
四、嫩黄色
一只藤条篮子,装着多半下剥出的褐红色蚕蛹。一个、两个,突然就无来由地摇了几下头(其实是尾)。
“买活的。”这是丈夫交代的。我从未吃过这种“蔬菜”,因此,不知道鉴别其死活的方法。但那能摇头的,应该是活的。可整整一篮子蛹,爱摇头、乐于证明自己还活着的,也就那么几个。
“都是活的。”——蹲在篮子后边那个脸又黑又皱的老头对犹豫不决的我这样说。我当然不相信他的话。——谁能说自己出卖的货色都早已寿终正寝,正在进行着不易察觉的腐烂?他肯定要说、反复地说,——都是活的,都是活的。
那几只摇头的,已在我的手里。这远远不够,怎么也得炒成一盘菜,于是我就抓了一把那一动不动的。
把那几个爱摇头的放在一个小碗里,准备留给儿子玩;其余的,就准备下油锅了。
油上的泡沫像云一样快速向天边飘散。油面风平浪静,但我知道,油开了,温度至少达到了三百度。三百度的油一声不响。——几厘米的深度,构成了一个无底的死亡深渊。
蛹倒进油里,那巨大的炸裂声,我是有准备的。我不只一次地往油锅里倾倒过东西:蔬菜、面团、肉片、虾仁。。。。。。我听惯了热油撕咬食物的喧哗,甚至有点悦耳。它和客厅里的家人、亲戚、朋友的说话声一起,共同构建了某一个假日、某一个节日的欢乐。
我是第一次往油锅里倒蚕蛹。这些正在以沉默和一动不动的方式孕育翅膀的生命,在遇油的一刹那,它们竟全都站立了起来!——一齐拼命地向我摇头!那至少有四十几个蛹,四十几个头齐刷刷地立着。它们在狂摇、在大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吓得连连后退,半天不敢呼吸。
——“它们都是活的。”那老头说的竟是一句真话。
我开始认真地看一只蛹。在能摇动的另一头,其实是它们的头。头上的眼睛、嘴、触须都在,连翅膀的一部分也在。只是这些东西都不像真的。——像模具。它们给自己弄好了模子,然后就照着自己的设计生长。——他它们的工作重点该是孕育翅膀。现在,他们停止了一切生命活动,集中所有生命力量孕育在他们看来十分重要的翅膀。因为过于专住和执着,它们就像死了过去。它们认为:没有翅膀的生活,有点可耻。根本没法活。于是它们停止了爬行,开始了自己的梦想。并为接近自己的梦想开始了禅定般的苦修。它们得一动不动,这是最基本的。那极少数爱摇尾巴的蛹,一定是精力不集中的蛹。它们极有可能长不出翅膀,或者长出极差的翅膀。它们的心不静。尾总想动,留恋自己蠕动的过去。——它们是蚕中的不纯洁部分。
我看着小碗里那几个仍在摇头摆尾的家伙,——我留下了它们中最俗劣的部分。
片刻,油锅中蚕的优秀分子们都不动了,它们惊醒后的大喊也哑了下去。——我中断了四十几个关于翅膀的梦想和努力。这时我发现:蛹在经历了死亡挣扎后,身体的样子大大地改变了:——它们的身体突然变长了,罗纹与罗纹之间的嫩黄色暴露了出来。
那些嫩黄色,在它们死亡之前是看不见的。就算它们忍不住“摇头”,要动那些关联,也是小心地注意着分寸。那些深处的嫩色稍一闪现,它们立刻慌张地遮住。现在,它们死了,在死亡的挣扎中,身体里的嫩黄色暴露了出来。它们已不能把它收拾回去、掩盖好。——那一定是蛹的害羞之处!
五、小战争
一开始,我不明白狗为何重视自己的排泄物。每次,在我清理时,都受到了来自它的顽强阻挡。
它的阻挡是有效的阻挡。60斤重、身高也超过了60厘米的成年金毛,和我一个中年妇女,是势均力敌的。这样,在和我对抗的时候,我并不能很容易地胜过它。经常是打成平手。而平手的结局就是没能很好地清除它的排泄物。
在它的排泄物中,它尤其珍爱自己的尿液。在我清除它的尿液的时候,我遇到的阻力也最大。有时,它见不能阻止我,会突然用整个身体扑在自己的尿上。出现几次这种局面后,我先用一只手拽住它,另一只手找到毛巾。它会甘心让我拽住吗?它的挣扎是很有力的。这导致我的清理过程急促、潦草、勉强完成。
——每擦一次尿,都是我们在打一个战争。
每一次,看起来都是它输了,我赢了。——不管它给予我的反抗多么激烈,我都艰难地擦了地板,清除了它的尿液。
这种战争我们一直在打。让我疑惑的是它既然总是输,它为什么不放弃?这种最后总是导致失败的战争它怎么就不厌倦?
我以为我赢了——我擦干净了地板。可是,它在我的胜利里并不沮丧,它的样子并不是完全输了。
后来我明白,一条湿毛巾,就算再加上一条干毛巾,是不能彻底打赢这个战斗的。我的胜利是宏观的;它的胜利存在于我看不见的地方,隐藏在地板缝中,或以分子的形式漂浮在空气里:这就是它每次都充满激情地和我战斗的原因。
它被它的胜利滋养着,使针对我的战斗越来越有战斗力。
看来一直是我在庆祝我的胜利;它在庆祝它的:我们都赢了。
狗是不爱洗澡的。虽然有些狗表现出爱洗澡的样子,那是为了取悦主人。它们不愿意洗掉自己身上的气味。——气味是它们的另一件外衣。这件衣服的作用不是保暖,是安全、自我存在的依据。把一只狗洗得无色无味或者很香,狗会相当恐慌。你用香皂把它洗香了,那等于你脱掉了证明它存在的衣服。它感到失去自己了,找不到自己了。它不知道自己还存在不存在,因为存在的依据没有了。它不喜欢香气。香气和它没有亲戚。香气不是它的衣服。香气不是它的依据。
人对狗的所为,尤其是卫生要求,是很残酷的。但是,狗不绝望。它们有办法找回自己。它们每天的排泄行为,跟人的完全不同。狗的排泄是有重要意义的。它们靠排泄物和空间建立可靠的联系。
它信心百倍地排出自己的气味,对抗人强加给他的气味。任何一只狗的一生,都是和主人战斗的一生。
我隔上几天就要用八四消毒液和来苏水把居室喷洒一遍。这时候,我的小狗惊恐不安。它紧紧跟着我,它不知如何阻止我。它团团转,没有办法。等我弄完了,它还是不停地走,不停地嗅,查看它的气味在我的狂轰滥炸后还剩下了多少。我每次这么喷药水,都是对它的一次毁灭性打击。它看着我这么做就像我看着家园被城管拆除。
我生病的时候,狗高兴了。我不能洒那破坏力极强的消毒液了;不能擦地板了;不能和它战斗了。屋子里积了厚厚的狗的气味,它暂时全面地赢了。连我都是狗的气味了,我失去自我了。
我无力地躺在床上,想着等病好了后,怎么清理这些我不喜欢的气味。怎么先把它关起来,彻底地打扫干净所有的房间。
2012年10月24日
六、搭救蜻蜓
我对蜘蛛的恐惧更多地来自它身后的那张弥天大网。这种网在蚊子以及蜻蜓看来一定是不存在的,就像人看不见未发生的灾难。
我一直警惕着蛛网,并且看得很清楚。它已经不能成为我的陷阱,但它使我走过屋檐和栅栏边时,如怕蛇的人走进山林。
我是在太阳将我晒得口渴,钻入黄瓜架下去摘一条带刺的小黄瓜的时候,迎面撞上那面掩映在黄瓜叶子里的蛛网的。蛛网很大,它将两根相距两米的竹竿连在了一起。我看见它的时候,蜘蛛不在网上,它躲了起来。但它决不会走远,它就在附近。网上已经有了一些收获。小的蚊虫,最醒目的是一只黄蜻蜓。它的翅膀被网粘住了,呈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倒悬在网上。我看见它时,它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死了。
看见一面蜘蛛网,我一般是迅速逃开。不管那网上有没有蜘蛛,我都会从后背漫上来一片冰凉的恐惧。我知道蜘蛛就在附近。而藏起来的蜘蛛更让我害怕。因为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躲才对。我一般是站住,一动不敢动,不敢再碰身边的任何叶子。然后全身肌肉紧缩,我会忘掉口渴,放弃唾手可得的黄瓜。如果我一时大意而一头撞上一面蛛网,那我会吓得接近于疯狂。会一边叫一边跑。我一定是在什么时候,被蜘蛛这种可怕的动物捕获过,在我用透明的翅膀挣扎的时候,将我一口一口地吞吃过。如果我掌握一个秘密而不说,给我用什么刑也许不奏效,只要拿来一只或大或小的蜘蛛,悬于我的头顶,并时刻有爬入我的衣领的可能,那么什么要紧的秘密我都会说了。蜘蛛就是我的天地,它吃掉过我。
在这种莫名的、不是来自经验中的恐惧里,我能接近一张莫测的蛛网,试图搭救那只倒悬的蜻蜓,如果不认为那只蜻蜓就是自己,我怎么能压住那荆棘般的恐惧。当我一想到一只黑蜘蛛从一片叶子的后边爬出来,顺着闪光的丝线接近那只蜻蜓,张开我从不敢细看的嘴,撕咬蜻蜓的身体,蜻蜓剧烈地抖动,我就全身收紧,打冷战。那一刻蜘蛛咬的就是我。
蜘蛛网上的蜻蜓,倒悬着,头朝下,尾朝上,以一个一头落入陷阱的姿势,落入了蛛网。
我不敢伸手把它摘下来,虽然这轻而易举。但我从来就不敢走近一张蜘蛛的网。我的办法是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或木竿,它的长度以能消减掉一部分我的恐惧,以使我能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而不惊恐地跑开,。竹竿的尖伸向网上的蜻蜓,死了的蜻蜓以为可怕的蜘蛛来了,突然痉挛似地抖动。它用了所以力气,以至整个蛛网都剧烈地抖动了起来。原来它没死。仅仅是它刚落入蛛网时的挣扎我没有看到。我看到它倒悬着不动的时候,它已经绝望了。我看到的是它的绝望。它被我弄到了竹竿的尖上。网出现了一个大洞。在这一搭救过程中,蜘蛛没有出现,它眼睁睁地看着留做晚餐的食物被一根木棍救走了。一定迷惑不解。它知道自己不是一根木棍的对手。因为它看见自己几乎是万能的网,对木棍无效。它于是理智地没有出击。我迅速带着那根等于是我延长了的手的木棍逃到安全地带。我用紧张得无力的手,将蜻蜓翅膀上的网摘掉。翅膀在这一过程中有了一些破损。当它重新飞起来时,形态有些滑稽,就像一个陂腿的人走路一样。
七、盒子里的布娃娃
我小的时候,有饭吃有衣穿。我没有饥饿记忆。食物总是很充足,衣服也很好。我妈会做灯笼袖、和平服、布拉加。我那时的生活比城里的孩子要好。我姑家的表哥表弟一放了暑假寒假就到我家来了。他们在城里吃不饱。至少是没有大米。我在温饱后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我要玩具。我想要一个布娃娃。我没有。谁都没有。前街的小丽没有;后院的堂姐也没有。我们大家都没有布娃娃。
七八岁后,我的手发育得很好了。我开始自己制作布娃娃。
在母亲的衣柜里,有她为我们制作衣服剩下的边角布块,但她习惯条理,不愿意我把她的衣柜翻乱。她是不允许我翻她的衣柜的,什么理由都不行。
尽管从母亲戒备森严的衣柜偷拿花布块的难度是如此之大,我还是成功地为我的布娃娃做好了一件粉色小衣服。她的裙子我想做绿色的。我利用母亲去五里外的韩国屯商店买油、盐、海带、布匹的至少两个小时的充裕时间,也未能找到我所期待的绿油油的一块布。最后,我选了一块白布。为我的第一个布娃娃做了一条白裙子。
我是不想为我的娃娃做白裙子的。白色多爱埋汰啊。我妈从来不穿白衣服,我们这些小孩也没有白色的衣服。白色与乡村没有亲戚。做完白裙子后,我找到了为她做白裙子的依据:我的娃娃她不用到田里去劳动,也不用去厨房煮饭,那致命的污泥和油渍就无法靠近她。
穿着白裙子的布娃娃躺在我的一个纸盒子里,我可以保证她不被生活弄脏。只要盖上那盒子的盖子,泥土、烟尘、脏了的手,就都被有效地阻挡了。
许多年后,当我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来到一所小学教书的时候,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自己买了一条裙子。——一条白裙子;第二年的夏天,我又买了一条裙子,还是白裙子。
我越来越像我幼年亲手制作的那个布娃娃。我像是那个布娃娃从纸盒子里走了出来。
我穿着白裙子给小孩上课;穿着白裙子走街串户家访;穿着白裙子去相亲;穿着白裙子进厨房煮饭;穿着白裙子上外地开会;穿着白裙子半夜回家……
我没有一个为我挡住油烟与尘土的纸盒子。我也没有我的布娃娃那么安静。我四处走,像个水银球一样,不肯在一个地方呆很久。我的白裙子注定会被弄脏。
八、君子兰今年为什么不开花?
我们家的君子兰,原来是一盆,后来发展成两盆。这盆花是有些说道。长着长着,就长成了两株,成为并蒂莲形式。后来为了每一株都能长得更好,我把它们强行拆散,分栽在两个花盆里。两株在一个盆里的时候就都开花,分开后,仍继续开花,没看出它们的心情有什么不好。在分割它们的时候,我看见它们的根部是长在一起的,我是用剪刀硬切开的。切开后我一度后悔,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切开,这会不会导致我的命运发生改变?它们和我之间存在象征关系?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就把两盆花挨着放。根分开了,叶子还联系着。这就像哥俩,小时候在一块,长大各自娶媳妇分家另过,但也还是一家人。
我们家的君子兰,一开始不是我们家的,是别人家的,被丢在楼梯间的窗台上,无人浇水,奄奄一息。我上班每天从她逐渐干枯的叶子下走过。总觉得是回事。一些天后,终于没能做到袖手旁观,临出门灌好一瓶子水,走到花盆下,踮起脚(楼梯间的窗台高,或我的个子矮。)往里倒水。水洒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被那植物胖手指一样的根部抓住了,握牢了。从此,我每周都这样踮起脚给它浇水。一边浇水我还一边联想,我可不要它转世变成个男的或女的,整日给我哭啊哭的,我给它浇水是不需要回报的。我这举手之劳可不用它下辈子还啊!我就是看不了什么东西在我的视野里慢慢死去。后来我感到这样太累,天下雨浇地球从来都不是用这种费劲的角度。我也想找个省力的角度浇水。我也感到这盆花是没人要的,我于是收养了它。
把它搬回家它就是我的了。我对待我养的植物可不是光给它浇点水,那哪是养花的正确态度?我对我养的动物、植物都是溺爱的。浇水那是最基本的,如同给孩子吃饭。我给它换土,给它施肥,又买一瓶子营养液。一番折腾,它很快就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到过年的时候,它就给我开花了。它开花有个好习惯,就是今年开花了,明年它还要开。今年春节时开花,明年还是春节时开花。从来不说我去年都开花了,累着了,那我今年歇歇不开花了。它像钟表一样走得很准。此后七八年,它年年不忘给我开一次花,现一次身。告诉我它的花是什么颜色的。不知不觉,我被君子兰惯出了毛病,它到时候开花,我就放心了。今年它没开花,到现在也没有一点动静。这盆不开,那盆也不开。像商量好了的。我感到这很不妙啊。我们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啊!我什么坏事都没干啊!它凭啥就不开花了呢?我得找谁去给评评理呢?这不要命吗?
如果我只有君子兰,它这一不开花,这种暗示给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像我这种树摇花颤都心惊肉跳的人怎能禁得住如此打击?我之所以在君子兰不开花的日子里,仍四平八稳地活着,是因为我及时地得到了另一个暗示的救援——我们家的米兰开花了!
在我的卧室里,还养有一盆米兰。它的来历与君子兰不同,是我于两年前在花市上花了大价钱买的。买时就不是幼苗,而是初具规模。是一棵小树了。在我家两年,它又把体积增大了至少两倍。两年前我费那么大劲抱它回家,原来它在今年君子兰不开花的阴翳日子里,救了我的命。它开花,用这个方式拯救我。
九、身体与世界的关系
在乡下小学教书时处过两个男朋友。他们一个是铁路工人,一个是粮库工人。在那个小镇,只有这两个单位:一个国营粮库,一个火车站。剩下就是农民了。我的至少两个女同学兼同事就嫁给铁路工人和粮库工人了。她们没有什么不适,这两个单位都工资高、待遇好。到什么时候单位就发什么。八十年代中期,一个铁路工人的工资竟然是我们这些教师的四五倍。两个结婚的同学,觉得这样的幸福生活不能独享,就从幸福里回过头,想把我也拉进去。那时我没有什么前途在那里明白地等着我,但是我不肯结婚,总觉得不对。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肯嫁给这两种工人。我从小的理想是要做皇后的。工人,工资再高,他能当上国王吗?那我还不如嫁给农民,那还是有一点希望的。后来我想最差也得找个诗人。诗人是可以自立为王的。就算他没有国土,没有人民。20岁时我脑子里被这些东西先塞满了,因此那高工资,对我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有一块比较坚硬的物质,不是物质财富就能打碎的。我不计较男人挣多少钱,我计较他是干什么的。我否定体力劳动,因为我认为,体力对世界的影响太有限了。身体太没有力量了。只要一颗子弹,你的身体就没了。如果你选择用你的身体直接接触这个世界,那么你就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从小就善良,爱为别人着想。这样我就没有当面说不。我就答应相处。没有把我发现的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说出来。见过两次面后,我再说不。如果是开火车的,我就说那他不是得老出差吗?老不在家我还结什么婚。如果他是粮库搬运工,我就问他小学毕业没有?我不问当事人,我没那么恶毒,我问媒人。我还达不到能欣赏原始美的高度,我陷在初级文明里,我能和体力劳动者相处、来往,但是不能结婚。我费这么大劲儿,把陡坡弄成斜坡,是怕女友伤心。因为,我等于否定了她们的幸福生活,那太伤感情了。我绕这么大弯子就是试图证明,我不是排斥某类人,而只是对某个个人不喜欢而已。不久,女友的脸上就带着淤紫来上班,我们都看到了,我不知道那是怎么了。原来工人丈夫工资高,脾气也大些。也有一小部分工人也是很优秀的。万一碰上也可以。但是我没碰上,都一般,不见优秀。
十、谁能把白墙看一辈子?
一入冬,我就有点儿反常。整个冬天,我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反常了。我是开春之后,偶然回头,才发现问题的。
在冬天,我无心上班,对工作提不起精神;无心写散文,对这个自己熟练的文体产生厌倦;不关心孩子,全班58个学生他考第55。数学和英语都打了30分。我不是个缺乏热情的人,也不是个善于合理分配热情的人。30分也不能使我紧张起来,这足够证明,我的热情全都放在了别处。我想,30分,天不会塌下来。上天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情,不会为此多下出一场雨或一场雪来,气温也不会因此再往下降了。
原来这些天我一直在买壁纸,我的热情全在壁纸身上。我原不知道壁纸会花费我这么多的热情,我以为到那里,买上就回家。谁知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乘我不注意已经变了。不知是些什么人,把壁纸的花样弄出那么多,一本一本的排列在靠墙的柜子里,像是几个世纪积存下来的经典。在桌子上,还一层层地码放着打开的样本。这就给我出了难题:我得在浩如烟海的花纹和颜色里做出选择。这是多么的困难。每一本壁纸样本,都是不同的世界。我做不到闭着眼睛拿起一本就走,我立刻变回儿童,想打开所有的本子,把整个世界都看上一遍。
十一、长生不老药
我对自己的归纳是——我是个有理想的人。我有许多个理想。他们大大小小,分布在我生命的不同时段上。小的都不说,单说那个最大的——我想长生不老,想万寿无疆,想在至少是非现实时间里永生。
我想在死了之后还能活着,不仅我的孩子记着我、怀念我,我还想让别人的孩子也记着我、怀念我。我想让我的笔名、原名,成为小学生需要背诵掌握的文学常识;想让我的生卒年月成为中学生考试卷上的一道填空题。我想让我的子孙在他读的课本里,突然就看见了他的祖先,穿越时间与他相遇。
我已成功地让我的读中学的儿子,在他的一堂语文课上,看见了那个每天给他洗衣煮饭的老妈的另一副面孔。这还远远不够,儿子之后还有孙子,孙子还会生儿子……这样下去,我和我的那些树梢上的孩子,将被时间阻隔。我走不过去,他们回不来。我见不到他们,他们见不到我。我在这头,他们在那头,我怎么才能与远在时间远处的我的孩子相遇?
肉体是个难题。肉体无法在时间中穿行。但是文字能。文字比肉体沉;文字比肉体轻。我得把肉体变形,把她打碎、分解,使之成为无限小、无限轻,使之能够轻巧地隐身于文字的内部。我要把自己缩小,小到可以藏匿在一个独体字里;轻到可以随一页纸飘。
由此,我找到了百年后与我的子孙相见的道路。
我要隐藏在一行诗里,一篇短文里,一部小说里,然后把我放在他们必经的路口,拦住他们,说出我是谁,说出我与他们的关系,说出我从哪里来。说出我被迫隐身变形才见到了他们。这是多么艰难的见面!这是多么有意义的见面!
现在,我每天写作。其实我是在做一个搬运工。我每天做的,就是将自己切成小块。然后,一块一块地搬离现在,移往他处,移往叙述时间。我现在努力干活,争取在我的肉体湮灭之前,把我的全部移走。移到那个可以永生的叙述时间里去。我将在那里重新聚合,组成一个完成的我。
我现在特别害怕死,因为搬运精神之我的工作,要由肉体之我来完成。我怕死,因为我的搬运工作才刚刚开始,离完全的抵达还远着那。如果走到一半我就死了,那么这个工作将无人接替,无人能代替我完成。我将成为一个中途的残局,一个无法收拾的残局、
因此,我得小心的活着,不抽烟、不喝酒、多吃水果蔬菜。精心维护血压、血糖、血脂的正常指数,尽最大努力延长自己的寿命。我热爱活着,因为我有任务。 |